传承弘扬创新
文章字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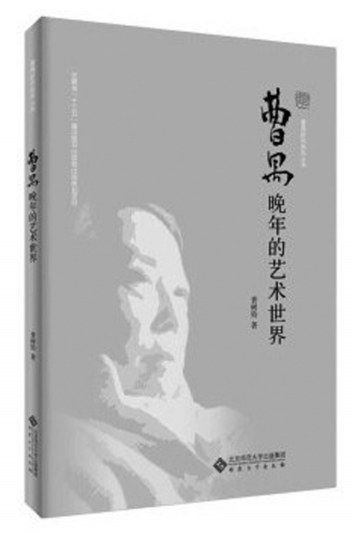
□施以钧
剧本是戏剧活动的基础和起点,探讨戏剧场面的开拓,对提高戏剧文本的艺术质量至关重要。
曹树钧先生从 1959 年到2014年,五十余载专心致志地“研究曹禺”,成果累累。如今他已年逾八旬,仍笔耕不辍,壮心不已,以饱满的热情关注曹禺剧作在全球的传承、弘扬、创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曹禺剧作活跃在全球五大洲25个国家的舞台上。
曹树钧先生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将教学与研究紧密相连,始终围绕着曹禺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和中国话剧史研究这三个内容。他用稿纸、钢笔备课,上课时用粉笔授课,讲得很仔细,且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曹树钧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时,他的毕业论文选题选择了《〈雷雨〉人物论》。让他感到荣幸的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顾仲彝教授。顾仲彝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是他引领曹树钧进一步领会了曹禺剧作的魅力,通过分析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戏剧大家对曹禺剧作多方面的影响,激发起了曹树钧在曹禺剧作研究上钻研的兴趣。
毕业后曹树钧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的写作依然很勤,闲暇中他去看了《雷雨》的实况转播,看完之后回家觉都睡不好,不停地寻思:这个戏怎么如此抓人?这个戏把30年前、3年前、3个月前复杂的经历压缩在一天一夜来表现,情节那么复杂,人物性格却如此鲜明,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作者写《雷雨》的时候只有23 岁,怎么23岁就写出了那么成熟的作品?
曹禺为什么23岁能够写出《雷雨》?这后来成为曹树钧先生的一个研究课题。
曹树钧也曾向我谈及诸家的文体。他极为推崇曹禺作品,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对于他自己的作品,却并不满意,其实他早年编写的《文艺理论》《中国话剧史》等教材,都是大手笔,可他觉得一点也不怎么样。他曾对我说:“这些教材如上高山,那是最低的山脚,也是起码的功夫。”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他现在每天坚持锻炼半小时,可以增强意志力和调节心情,提高免疫力。平素还有点喝茶的嗜好,他说,喝茶能让人在繁忙的生活中静下心来,品味这一杯茶,就如同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不过,他有时会得点小病,不喜就医,“不服药,过两天就好了!”《曹禺晚年年谱》《曹禺晚年的艺术世界》等都是他努力钻研及探讨曹禺生平的专著,而且校样也是自己亲自看。
曹树钧先生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剧作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从《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成才之路》《曹禺剧作演出史》《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到《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曹禺晚年年谱》《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等,直至晚年他创作了《曹禺晚年的艺术世界》,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学术难题的攻克相映成趣,力图以形象思维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与逻辑思维的清晰性和排他性形成互补。他还多次谈到,还有一些领域,例如曹禺的教育思想、曹禺的艺术管理思想、曹禺的戏剧理论、曹禺对外文化交流的贡献,等等,基本上尚未系统展开,需要进一步开拓。
读他的曹禺剧作研究,文字刚柔并济,所以他的《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21世纪莎学研究》等书,虽有推陈出新之意,但比起他的曹禺研究作品的成就,略逊一筹。这话,是他在上海戏剧学院咖啡馆里和我说的。他说,莎士比亚可以说是曹禺最推崇、最敬佩的一位戏剧大师。
曹树钧先生的曹禺研究始于1959年18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今天看来,读曹树钧先生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老校友致敬的意味,当然,也带有曹树钧先生鲜明的个性。结合曹树钧先生发表的《曹禺晚年年谱》可以看出,曹树钧先生进入学术成熟期的标志就是对作家艺术风格的解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进入21世纪以来,曹树钧先生的曹禺研究以更加全面、深入的态势展开,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向新的方向拓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