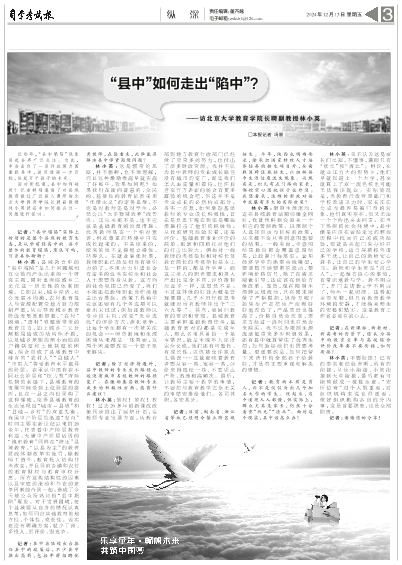“县中”如何走出“陷中”?
文章字数:
□本报记者 冯丽
近些年,“县中塌陷”现象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为此,中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图重振县中,进而造福一方百姓,托起万千孩子的未来。
面对新机遇,县中如何破局?记者特别邀请了对县域教育做过广泛深入调研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就县中如何振兴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记者: “县中塌陷”实际上折射的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是从学前到高中的、县乡整体的教育塌陷,您认可吗,可否具体聊聊?
林小 英:县 域教育 中的“县中塌陷”是几个问题域相互交错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研究主题,同时也面临城乡二元化 这一 历史性 的体 制困境。长期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农村教育投入与资源配置受地方财力限制严重,从而导致城乡教育阶段发展差距显著。“在村”困境、“离村”难题所带来的教育压力,加上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面临的户籍 制度 和土地 制度 的困境,综合形成了县域教育中特有的“农村人”“县城人”“市里人”等受教育水平迥异的阶层。在承认中国存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压力型”府际机制的前提下,县域教育的发展空间受到上位阶层的挤压,且在一县之内也同构了这种梯度,使得县域教育的生态呈现出“城市-县域”和“县城-乡村”的双重失衡。我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发育”时间主要在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代表着中产阶层教育利益、充满中产阶层话语的“城市教育”同样在“挤压”县域教育。“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实施后,除教师工资外,教育投入结构并未改变,并且导致乡镇和农村的教 育财 权与教 育事 权分离。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以及家庭的流动和外在的竞争因素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今天被公众所熟知的“县中塌陷”现象。对于发展困境,每个县域要从自身的情况认真思考,如何回归基础教育的地方性、个体性、成长性。若实在没有明确方案,就少干预、多投入、迟评价、弱竞争。
记者:在中省陆续出台振兴县中的政策后,不少县中推出高薪,包括年薪招聘优秀教师,在您看来,此举能否解决县中师资困境问题?
林小 英:这 是惯 常的思路,并不新鲜,也不难理解,而且这种激励措施早就实施了好些年,效果如何呢?如果我们在面向普惠的、全民的、基础性的教育依然采用“优绩主义”的定势思维,不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必然会以“大多数被放弃”而告终。这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基础教育的治理措施。优秀教师是在 一个相 对宽容、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自我成长起来的。不是挖来的,挖来的也不见得能立得住、站得久。在就业紧张时期,教师职业已经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了,不用大力引进也会有诸多的优秀在校生和社会人士想要终身从教。这方面的社会氛围已经变了,我们不能还把教师职业当作洼地去出台措施。政策工具箱中应该还要有几个备选项可以拿出来试试:例如还教师以专业自主权 、改变“优中选优”的评价方式、淡化竞争、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次被关注的机会……师资困境和生源困境从来都是一体两面,这两个困境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来解决。
记者:除了经济待遇外,县中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也远没有城市名校教师的路径宽广。在激励基层教师专业成长的积极性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林小英:放权!放权!放权!过去20多年的新课改政策同步推出了国培计划,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财政资源。我并不认为县中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没有城市的宽广,而是我们怎么去度量和看待,也许后者在官方表彰的场合有更多露脸的机会吧,但这并不是专业成长的必然构成部分。务实一点想,如何激励基层教师的专业成长积极性,首先是反思下现在到底是哪些措施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我的研究经验来看,还是评价。基础教育事业评价的简单、粗暴和同质化对他们的打击比较大。例如对一线教师的考核指标和对校长及教育局长的考核指标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升学率。而这三类人的职责要求和投入产出比完全不同,评价指标却近乎一样,这显然不妥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大概是管理便捷,几乎不用仔细思考就能对所有教师排出个“三六九等 ”。其次,要回归教育的常识和常规。县域教育主要承担基础教育任务,基础 教育面 对的 都是 未成 年人,那么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未成年人还没完全长成,他们还有可塑性、有成长性,应该被允许犯点儿错误……这就意味着教育者要从容一些、宽容一些,评价来得宽松一些,不要那么严苛、迅速和高频次。最后,让教师主要干教学的事情,不要把与教育教学完全无关的事情安排给他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分。
记者:目前,湖南省、浙江省等地已经明令禁止跨区域招生。今年,陕西也明确要求,除承担国家特殊人才培养任务的招生项目外,全面取消跨区域招生,以扭转县中生源过度流失现象。而现实是,但凡有点门路的家长,都挖空心思把孩子往外送。在您看来,这样的新政对县中发展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林小英:限制生源流动,这在县域教育话题引爆全网时,我就预料到会迎来一个相应的管制政策。以限制个人选择自由为目标的政策,从来都不会只得到意图想要的结果。一般来说,非意图结果最后都会覆盖意图结果,让政策目标落空。套用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模型,要调整市场要素的流动,要影响价格信号,除了在需求端做引导,还应该在供给方做改革。显然,现在限制生源跨区域流动,只在需求端做了严格限制,供给方呢?如果生产者把生产流程好好地改造了,产品质量也提高了 ,价格自然会改变,需求方经过一段时间也自然会来购买。我不认为限制生源流动能带来多少积极效果,还有县中就算留住了优秀生源,如何教好他们也需要考量。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留下来读书的全部孩子给教好,才是真正要重视和解决的事情。
记 者:教育的 本质是 育人,而不是仅仅为出几个知名大学的学生。说起来,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实际上,群众尤其是家长,仍然十分看重“状元”“清北”。面对这个现实,县中该怎么办?
林小英:我不认为这是家长们无知、不懂事,满眼只有“状元”和“清北”。相反,在就业压力大的形势下,他们早就知道上一个大学,甚至就算上了双一流名校也可能无法保证就 业。 实际情况是,当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改进乏力时,家长往往会成为最容易被归咎的对象,他们真实存在,但又无法一个个拎出来去问责。在当下热闹的社会环境中,县中倒是应该在曾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找回自己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关起门来办好自己的学校,适当屏蔽校外诸多干扰,让自己的教师安心教书,让自己的学生安心学习。教师和学生都是“自己人”,一起做有良心的事情,有常识地教与学。教不明白了,开门去请教 ;学不明白了,师生一起切磋。这看起来很无聊,但只有教育教学环境的安静,才能换来师生的安稳和踏实。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有的心态。
记者:在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的背景下,您认为县中的教育变革与高校综合评价改革要不要衔接,如何衔接?
林小英:不要衔接!已有的事实和经验表明,所有的衔接,从幼小衔接 、小初衔接到大中衔接,最后都有可能被做成一桩桩生意。“安所位育”对个人很重要,对组织机构来说也很重 要 。做好组织机构各自的分内事,这是首要职责,也是全部职责。
记者:谢谢您的分享!
近些年,“县中塌陷”现象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为此,中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图重振县中,进而造福一方百姓,托起万千孩子的未来。
面对新机遇,县中如何破局?记者特别邀请了对县域教育做过广泛深入调研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就县中如何振兴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记者: “县中塌陷”实际上折射的是整个县域的教育生态,是从学前到高中的、县乡整体的教育塌陷,您认可吗,可否具体聊聊?
林小 英:县 域教育 中的“县中塌陷”是几个问题域相互交错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研究主题,同时也面临城乡二元化 这一 历史性 的体 制困境。长期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农村教育投入与资源配置受地方财力限制严重,从而导致城乡教育阶段发展差距显著。“在村”困境、“离村”难题所带来的教育压力,加上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面临的户籍 制度 和土地 制度 的困境,综合形成了县域教育中特有的“农村人”“县城人”“市里人”等受教育水平迥异的阶层。在承认中国存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压力型”府际机制的前提下,县域教育的发展空间受到上位阶层的挤压,且在一县之内也同构了这种梯度,使得县域教育的生态呈现出“城市-县域”和“县城-乡村”的双重失衡。我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发育”时间主要在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代表着中产阶层教育利益、充满中产阶层话语的“城市教育”同样在“挤压”县域教育。“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实施后,除教师工资外,教育投入结构并未改变,并且导致乡镇和农村的教 育财 权与教 育事 权分离。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以及家庭的流动和外在的竞争因素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今天被公众所熟知的“县中塌陷”现象。对于发展困境,每个县域要从自身的情况认真思考,如何回归基础教育的地方性、个体性、成长性。若实在没有明确方案,就少干预、多投入、迟评价、弱竞争。
记者:在中省陆续出台振兴县中的政策后,不少县中推出高薪,包括年薪招聘优秀教师,在您看来,此举能否解决县中师资困境问题?
林小 英:这 是惯 常的思路,并不新鲜,也不难理解,而且这种激励措施早就实施了好些年,效果如何呢?如果我们在面向普惠的、全民的、基础性的教育依然采用“优绩主义”的定势思维,不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必然会以“大多数被放弃”而告终。这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基础教育的治理措施。优秀教师是在 一个相 对宽容、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自我成长起来的。不是挖来的,挖来的也不见得能立得住、站得久。在就业紧张时期,教师职业已经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了,不用大力引进也会有诸多的优秀在校生和社会人士想要终身从教。这方面的社会氛围已经变了,我们不能还把教师职业当作洼地去出台措施。政策工具箱中应该还要有几个备选项可以拿出来试试:例如还教师以专业自主权 、改变“优中选优”的评价方式、淡化竞争、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次被关注的机会……师资困境和生源困境从来都是一体两面,这两个困境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来解决。
记者:除了经济待遇外,县中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也远没有城市名校教师的路径宽广。在激励基层教师专业成长的积极性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林小英:放权!放权!放权!过去20多年的新课改政策同步推出了国培计划,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财政资源。我并不认为县中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没有城市的宽广,而是我们怎么去度量和看待,也许后者在官方表彰的场合有更多露脸的机会吧,但这并不是专业成长的必然构成部分。务实一点想,如何激励基层教师的专业成长积极性,首先是反思下现在到底是哪些措施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我的研究经验来看,还是评价。基础教育事业评价的简单、粗暴和同质化对他们的打击比较大。例如对一线教师的考核指标和对校长及教育局长的考核指标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升学率。而这三类人的职责要求和投入产出比完全不同,评价指标却近乎一样,这显然不妥 。不过这样做的好处大概是管理便捷,几乎不用仔细思考就能对所有教师排出个“三六九等 ”。其次,要回归教育的常识和常规。县域教育主要承担基础教育任务,基础 教育面 对的 都是 未成 年人,那么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未成年人还没完全长成,他们还有可塑性、有成长性,应该被允许犯点儿错误……这就意味着教育者要从容一些、宽容一些,评价来得宽松一些,不要那么严苛、迅速和高频次。最后,让教师主要干教学的事情,不要把与教育教学完全无关的事情安排给他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分。
记者:目前,湖南省、浙江省等地已经明令禁止跨区域招生。今年,陕西也明确要求,除承担国家特殊人才培养任务的招生项目外,全面取消跨区域招生,以扭转县中生源过度流失现象。而现实是,但凡有点门路的家长,都挖空心思把孩子往外送。在您看来,这样的新政对县中发展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林小英:限制生源流动,这在县域教育话题引爆全网时,我就预料到会迎来一个相应的管制政策。以限制个人选择自由为目标的政策,从来都不会只得到意图想要的结果。一般来说,非意图结果最后都会覆盖意图结果,让政策目标落空。套用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模型,要调整市场要素的流动,要影响价格信号,除了在需求端做引导,还应该在供给方做改革。显然,现在限制生源跨区域流动,只在需求端做了严格限制,供给方呢?如果生产者把生产流程好好地改造了,产品质量也提高了 ,价格自然会改变,需求方经过一段时间也自然会来购买。我不认为限制生源流动能带来多少积极效果,还有县中就算留住了优秀生源,如何教好他们也需要考量。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留下来读书的全部孩子给教好,才是真正要重视和解决的事情。
记 者:教育的 本质是 育人,而不是仅仅为出几个知名大学的学生。说起来,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实际上,群众尤其是家长,仍然十分看重“状元”“清北”。面对这个现实,县中该怎么办?
林小英:我不认为这是家长们无知、不懂事,满眼只有“状元”和“清北”。相反,在就业压力大的形势下,他们早就知道上一个大学,甚至就算上了双一流名校也可能无法保证就 业。 实际情况是,当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改进乏力时,家长往往会成为最容易被归咎的对象,他们真实存在,但又无法一个个拎出来去问责。在当下热闹的社会环境中,县中倒是应该在曾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找回自己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关起门来办好自己的学校,适当屏蔽校外诸多干扰,让自己的教师安心教书,让自己的学生安心学习。教师和学生都是“自己人”,一起做有良心的事情,有常识地教与学。教不明白了,开门去请教 ;学不明白了,师生一起切磋。这看起来很无聊,但只有教育教学环境的安静,才能换来师生的安稳和踏实。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有的心态。
记者:在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的背景下,您认为县中的教育变革与高校综合评价改革要不要衔接,如何衔接?
林小英:不要衔接!已有的事实和经验表明,所有的衔接,从幼小衔接 、小初衔接到大中衔接,最后都有可能被做成一桩桩生意。“安所位育”对个人很重要,对组织机构来说也很重 要 。做好组织机构各自的分内事,这是首要职责,也是全部职责。
记者:谢谢您的分享!